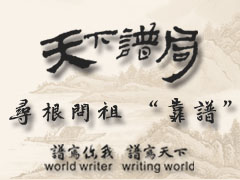早期大埔人文历史进程与茶阳饶氏
士大夫渊源初探
饶宝忠
本文试从建县早期----明朝----清朝中期这一時段来初步分析茶阳饶氏士大夫在大埔县人文历史中所起的作用和渊源。在这一時期,正是茶阳饶氏宗族从小发展壮大,科举名人从少到多的時期;也正是在历代饶氏士大夫的感化下,大埔从蛮荒之地慢慢变为文明古邦,客家圣地的時期。本文所称茶阳以前是为大埔县城。
据县志称:大埔在设县前,是嶺南一个瘴氣寒熱,盗贼蛮荒之地。境内层峰叠嶂,县民环山而居。元史地理志称:潮州路神泉村位于广东省东北部山区,十五年歸附元朝,十六年改爲總管府,以孟招討鎭守,未幾移鎭,漳州土豪随即占據二十一年。后廣東道宣慰使月的迷失(蒙族人名)以兵招諭,二十三年復爲江西等處行樞密使兼廣東道宣慰使以鎭之,潮州府志称,長汀涂某以鹽徒來神泉村,於茶山下築城聚衆,號曰涂寨,自稱侍郎,占據上杭、金豐、三饒、程鄕之地,私徵賦稅,傳弟涂僑盤踞二十餘年,至元二十一年,甲申安撫使月的迷失討平之。
明洪武二年改潮州路爲潮州府,成化十四年析海陽八都置饒平縣。饒平建邑後,猶以洲二都遠饒,治輸賦維艱,且峒民时时作梗。意即在明代中期以前,这一地区在行政上属海阳县辖地,因“僻远官府,政教难逮”,山中所聚多梗化之民。成化十四年,明王朝在征剿这一带的盗贼时,为加强控制,设立饶平县。饶平县设立后,这里仍然是“法度不行,教化不及之地。
此时,茶阳饶氏从汀州迁来已传到第七世。其中饶金在成化十三年(1477)“以春秋领乡荐,历官至剑州知州”。他的弟弟饶监则受学于明代大儒江门陈白沙。在各种版本的《大埔县志》“人物志”中,这两个人分列在“宦迹”与“儒行”之首。更重要的是,饶金在辞官乡居时,出面提议设立大埔县。
嘉靖四年,应茶阳饶金(茶山公)所倡,巡撫熊蘭疏請置縣,嘉靖五年析饒平洲淸遠二都置大埔縣。据谱载:饶金于正德五年(1510)擢升四川剑州知州。他以淸远、恋州二都,远隶饶平,管治鞭长莫及,民生无法保障,乃请求朝廷割清远、恋州二都,创置大埔县,以塞盗源。饶金的创意得到民众拥护,最终获朝廷批准。盖倡置大埔县,饶金实为第一人。会奏报允,乃于嘉靖丙戍设大埔县治,后盗戢民安。嘉靖四年(1525)卒,饶金入乡贤祠。
据查,在明代,广东很多新设县都与弭盗的目的相关,而且往往都是在本地势力的推动下发生的,顺德、新安等县的设立都是如此。饶氏家族在大埔设县中充当的角色,既是基于该家族在本地的影响,又毫无疑问强化了这种影响,奠定了饶氏后来成为大埔县望族的基础。
设县之后,其实大埔仍然是山盗海寇活跃之地,但同时也是商业贸易的交通要道。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本地的饶氏权势人物极力利用各种资源同明王朝拉上关系,建立起正统化的社会秩序。饶金中举出仕之后的茶阳饶氏家族,开始按照士大夫的作派,理学家的主张,按照古代宗法原则,再根据当时的社会现实加以变通,来建构地方宗族的规范,再以宗族规范来教化和影响周边的民众。这是明代中期以后地方士大夫建立地方社会文化认同的一个重要途径。
明代宗族社会的建构,是由地方上控制了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的饶氏士大夫势力去实践的,因此这也是在地方社会借助正统化的文化资源去树立权威和维护权力的手段。最辉煌的时期有两个,一是明朝饶相、饶与龄“父子进士”以后。一是清朝饶芝、饶褒甲“父子进士”时期。
“士大夫”一词是中国固有的词汇,传统中国各阶层中与皇庭最接近的群体是“士”,但“士”与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有本质区别,传统中的“士”是四民之首,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都享有巨大权力,政治上,“士”是社会的领导阶层,整个官僚系统由他们掌握;在文化上,“士”享有对道统的解释权,对上可以劝谏帝王,对下可以教化万民。因此,在传统中国社会,“士”处于绝对重心地位。决定士大夫中心地位的关键在于科举制度。
明清科举制度已经完善、士大夫阶层崛起、租佃制盛行等。对人文的关怀及知识的普及,使宗族礼仪文化向社会各个阶层普及,各个阶层都开始接受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根据的礼教。本县地方社会的运行中饶氏士大夫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他们社会使命感、责任感空前增强,以重整社会秩序为己任,主动通过多种途径有意识的对地方民众进行宣传教化。正是由于他们的教化活动,才将儒家倡导的理念深入贯彻到县民之中。
在古镇茶阳。至今保存有许多明清时期的饶氏祠堂屋,如:大宗祠、世魁祠、太史第、冬官第、诒榖堂、仙瑞堂、明经祠等等,据老辈人讲,最多时有三十多间较大型的饶氏祠堂屋。这些祠堂屋既是居屋、宗祠,又是饶氏子孙和乡民的学堂。饶氏士大夫们在宽大祠堂厅堂里讲授与培养忠君、孝亲、恭敬、诚信的内容。使宗亲和乡民直接受儒家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饶氏宗族还通过旌表、劝谕、禁断活动张扬符合儒家道德价值观念和伦常礼教标准的行为。劝谕子孙遵从儒家的伦理规范,使当地社会形成互相礼让、尊老敬老的社会风气。达到息狱讼、除盗贼、美风俗的目的,维护了社会的稳定。饶氏士大夫鼓励子弟读书,在日常生活中以自己的行为对家人施加影响,家内教化的成效非常显著,在地方社会也产生示范性的影响。士大夫还在地方社会中也会采用各种方式教化地方民众。倡导订立乡约、乡规、协助或自己兴办各种学堂、日常生活中履行博施济众的观念等行为在民众中树立起自己的威望,为人们做表率,在当地社会中发挥了很好的教化作用。不经意间,饶氏士大夫在主动地、有意识地对乡民进行教化。
我们再从茶阳饶氏人文历史脉络来看:从明朝到清朝中期,饶氏族人中有“将仕郎”、“应例承事郎”、“恩赐冠带”,“知州”,“儒学大家”、“郡禀生”,“郡庠生”,“冠带义官”,“千户公”、“七品散官”,“冠带义官”,“奉直大夫”“朝议大夫”、“太史”、“邑庠生”、“增广生”、“县丞”、“进士中书舍人”、“应例儒官”、“增广生”、“中书舍人”、“鸿庐寺序班”、“司训”、“学训”、“教谕”“恩授儒官”、“光禄寺监事”、“课务钦差”、“县尹”、“知州”、“知府”、“进土”、“举人”、“贡生”等功名职官者多得数不胜数,简直是一本科举和职官的教科书。据茶阳饶氏族谱记载:至清朝中期,族中有科举功名之人(进士、举人)已在百外,还不包括清朝中期以后的进士、举人。在茶阳这个只有几平方公里的小县城内。讲俗一点:有一个饶氏祠堂放喜炮,整个县城都能听到。有这么多的文人士大夫,平时的教化作用可想而知。从凡夫俗子的角度来看,小县城里常有饶氏族人取得功名回来后,都会有“骑大马,鸣大锣,游大街”的仪式进行,可见读书考取功名,这对当地的男性青少年坐有何等的吸引力?不言自明。诚然,饶氏士大夫们也就成了乡民的榜样和精神偶像。
故此笔者认为,早期大埔人文历史的进程与茶阳饶氏士大夫的言传身教有着极深的渊源。正是由一代又一代的饶氏绅衿士大夫们悉心经营,在当地扮演着“树仪型,胥教化”角色的一个大族,才将一个蛮荒之地改变为崇文重教的礼仪之县、客家人文圣地。直到今天,在原大埔县城茶阳,最为瞩目的仍然是为饶氏士大夫树立的“父子进士牌坊”,几百年来,这个牌坊竖立在县学宫前,彰显着饶氏宗族在本地的声望和地位。至今,每天都有许多海内外的游人慕名来到茶阳,参观考察饶氏人文古迹,这是不是可以说,茶阳饶氏人文历史还在大埔起教化作用呢?
本文资料来源:《大埔县志》《饶氏族谱》《宗法、户籍与宗族·刘志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