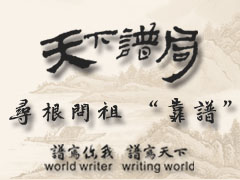9月25日上午,突然得到饶子健同志逝世的消息,难以名状的悲痛,顿时涌上心头。多年并肩战斗的情景,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9月25日上午,突然得到饶子健同志逝世的消息,难以名状的悲痛,顿时涌上心头。多年并肩战斗的情景,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我与子健相识于六十年前的抗日战场。1940年春,我新四军第六支队在豫皖苏敌后发动群众,打击日伪,根据地正处于大发展时期。由于支队的主要成分都是根据地的青年群众,没有红军的部队作基础,骨干缺乏。因此,急需大批有经验的军政领导干部。
一天,支队司令员兼政委彭雪枫同志对我讲:“党中央、毛主席从延安给我们派来了一批干部,明天就到新兴集。你负责接待一下。”新兴集在安徽省涡阳县,是支队司令部所在地。次日晨,我去镇口迎接他们。子健同志是带队的,同来的还有姚运良、周纯麟、吴先党等同志。他们的到来,使支队增添了新的骨干力量。我与子健一见如故。经过交谈,得知他们都是红军干部,经过长征的考验。子健等同志还随西路军西征,历尽艰辛,在李先念同志率领下,突围到新疆,后又转赴延安的。特别是听到饶子健同志带着先头部队,杀出一条血路,在新疆境内,与前来迎接的我党同志取得了联系。我真为我们支队增添了这员勇将而高兴。
那时,六支队下辖三个团、四个总队和三个独立团。开始,组织上安排子健同志担任第三团团长。不久,八路军第二纵队南下,到达豫皖苏边区,我支队奉命与之会合。组成了八路军第四纵队。子健所在的团队改番号为四纵队六旅十六团,他仍任团长。其时,六旅旅长谭友林赴延安准备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纵队党政军委员会认为,子健同志政治可靠,军事上也很强,作风正派,遂决定由他代理旅长职务。
皖南事变后,八路军第4纵队又改编为新四军第四师,子健同志领导的六旅也改编为四师十二旅。面对日伪军的反复“扫荡”,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在敌、伪、顽的夹击下,我们豫皖苏边区进行了三个月艰苦卓绝的自卫作战。尔后,从津浦路西转移到津浦路东的洪泽湖地区坚持斗争,度过了抗日战争中最困难的岁月。1941年10月,为适应对敌斗争的需要,十二旅进行了整训和缩编,一部补充了其他部队,一部组建了苏皖边区的淮北军区。子健同志任军区副司令员,积极发展地方武装,为恢复与坚持淮北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全国解放战争中,我同饶子健同志更成为亲密战友。1945年冬,华中分局和华中军区决定,由新四军第四师十一旅、十二旅的主力编成华中野战军第九纵队,由我任司令员兼政委,子健同志任副司令员。1946年初,我与子健同志会合,在安徽灵璧县高楼宣布九纵队正式成立。从此,我与子健同志朝夕相处,一起领导着这支由淮北地区抗战子弟兵组成的野战兵团。
1946年7月以后,面对国民党军向我华中解放区的大举进攻,我纵队在山东野战军陈毅司令员的统一指挥下,先后参加了朝阳集、泗县、两淮和宿北等重要战役。子健同志作战指挥坚定沉着,英勇顽强。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他总是主动要求到主要方向上去,到最困难的地方去。在为保卫华中解放区首府淮阴的运动防御战中,我纵队首当其冲,与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七十四师反复拼杀。在华中野战军谭震林政委统一指挥下,子健同志几次亲率部队,向蜂拥而至的敌军实施反冲击,与五和十三旅等部共同战斗,有力地顿挫了敌人的进攻气焰。
在作战中,子健同志注意观察战场情况的变化,及时作出处置,并能提出很好的建议。在宿北战役中,我九纵担负宽大正面的防御任务,阻击敌整编十一师与六十九师向沭阳、新安镇方向进攻,以待山东和华中野战军主力到来,共同歼敌。一日,子健同志在阵前观察到敌人频频调整部署,判断其可能要撤退,我军宜立即行动,便报告了粟裕司令员。粟司令员立即定下决心,发起进攻,打乱了敌人,加速了战役的胜利进程。
宿北战役后,中央军委曾计划九纵与从淮北地区撤出的华中第七军分区部队合编,重新打回被敌人占据的淮北根据地,并决定由我兼任淮北地委书记。受领了这一任务后,我与子健同志都信心百倍。因为这是我们在抗战中长期坚持与发展起来的,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养育与支持了我们这支人民军队,彼此有着深厚的感情。就是再困难,我们也一定要站住脚,坚持发展敌后游击战争。
后来,战争规模越打越大,华中分局建议,既要派出开辟敌后战场的部队,也要保持正面战场上拥有迎击敌军的强大力量。最后决定,将华中野战军第九纵队一分为二。由我率领三个团恢复第十一旅番号,留在正面战场,与山东野战军二纵第四、九两旅合编为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由子健同志率领九纵另外两个团及骑兵团一部,组成淮北挺进支队,子健任司令员兼政委,重返淮北,执行坚持敌后的任务。我们都深知,留在敌后,要根据当时情况独立地定决心,责任更重,任务也更艰巨。这次分手,不知何时才能再见面。1947年1月,淮北支队向敌后挺进时,我将子健送到运河边。我们紧紧握手,互致祝愿。难舍难分的情景,我至今历历在目。
本文来源:http://ewen.cc/books/bkview.aspx?bkid=215031&cid=660629